上海之春|“八季”:年轻的《中国四季》致敬三百岁《四季》
- 情感
- 2025-04-09 12:34:05
- 22
1725年,维瓦尔第包含四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第八号《四季》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今年是《四季》诞生三百周年。4月3日晚,小提琴家吕思清和美杰新青年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了“永恒的四季”音乐会,以维瓦尔第《四季》搭配青年作曲家文子洋新创的《中国四季》为“三百岁”的《四季》庆生。两部作品一老一新,老作品四季常青,新作品创意迭出,音乐会再现了维瓦尔第不朽杰作的无限生命力,以及《四季》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
维瓦尔第标题为《四季》的巴洛克时代的协奏曲与同期的其他大协奏曲有着显著不同,无论是连同乐谱一同印刷的描写四季场景的十四行诗还是对每个乐章描述性的文字都起到了标题音乐应有的作用:指向性。借助于描述性的文字和形象的音乐,人们得以在音符中体会到四季更替带来的节气变化。在维瓦尔第的笔下,声音被赋予了冷热、干湿、阴晴和日夜的情景表达,继而仿佛可以被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感知到。

吕思清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八季”
虽然作曲家在1710-1730年间写了不少带有明确指向性的乐曲,描绘布谷鸟、牧羊女、狩猎和海上风暴,但像《四季》这样以40余分钟的完整体量惟妙惟肖地呈现一年四季的套曲极具创新意识和前卫精神。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会前任总监,音乐学家尼克拉斯·肯杨爵士(Sir Nicholas Kenyon)便认为,乐曲的创新体现在纯器乐被赋予前所未有的画面感和故事性,足以精准描绘气候、环境和人的心理变化;前卫性在于打破了巴洛克时代协奏曲的规制,三到四分钟短小精悍的每个乐章更像是为如今快餐文化度身定制的快节奏的“短视频”。在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副教授朱洋看来,乐曲永恒的魅力还在于通过描写大自然,折射出环境保护意识,与当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
基于此,乐曲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束之高阁,少有问津。直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乐曲诞生近两百年后,巴黎才出版了《四季》的双钢琴谱,那是乐曲真正被大众接受,进入广泛视野的标志。进入录音工业迅猛发展期,音乐随着唱片的录制发行真正复兴,风靡全球。
深为《四季》着迷的自然有小提琴家。这套为弦乐而写的协奏曲吸引着从本真运动先驱到思想不羁型男的音乐家的目光。除了特雷弗·匹诺克、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帕尔曼、祖克曼和敏茨等遵照巴洛克风格“祖制”的录音之外,梳着朋克发型的英国小提琴家尼盖尔·肯尼迪在1989年与英国室内乐团以极具摇滚风范的演奏让《四季》成为了流行文化的先驱。小提琴家如陈美、基顿·克莱默乃至丹尼尔·霍普的成名或多或少都与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演奏《四季》并一炮打响有关。《四季》一时间成了小提琴家出类拔萃、标新立异的“试金石”。
极富创意和前卫的乐曲同样启迪了一批作曲家以四季为题,其中就有海顿的清唱剧,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施波尔(Spohr)及拉夫(Raff)的交响曲、格拉组诺夫及约翰·凯奇的芭蕾舞剧和帕努夫尼克(Roxanna Panufnik)2012年为小提琴为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
作为“梗王”的《四季》除了被包括《辛普森一家》的影视剧和广告片引用片段之外,也催生了两部魔改大作。马克斯·里希特的《重组·四季》在保留维瓦尔第原曲结构和织体的同时,引入了现代化的和声和电子音乐特效,2022年在上海夏季音乐节由金郁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上演,让听众体验到里希特标志性的慢条斯理的魔力。
远在南半球,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加进班多钮和钢琴,以探戈元素魔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不仅是向《四季》致敬的杰作,更是凭借基顿·克莱默2000年出版的唱片成为音乐会标准曲目。维瓦尔第来自巴洛克时代的意大利,皮亚佐拉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根廷,两人的作品一古一今,一北一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久而久之,人们惯于把维瓦尔第和皮亚佐拉的两部作品安排在同一场音乐会的上下半场,组成“八季”演出,呈现出音乐上有趣的对话和反差。这一做法在国内亦广为接受,2023年12月12日吕思清与美杰新青年乐团在海口的海南岛国际音乐节,2025年4月11日陈锐与上海交响乐团弦乐演奏家在第二届左岸音乐节上演的“八季”音乐会均属此例。
《四季》的影响力辐射南半球,也远及东半球。数位中国作曲家先后以四季为题创作,完整覆盖到民族管弦乐、室内乐和弦乐重奏,无不反映出中国独特的文化地貌。

苏潇《莫愁》在江苏大剧院首演
2021年,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苏潇受南京民族乐团委约创作民族管弦乐《莫愁》,便在第一乐章中以十分钟的短小精悍篇幅呈现了莫愁湖的四季,表达了“春水流声、夏日蝉语、秋风过耳、冬雪飘扬,四季在莫愁湖上雕刻时光,画意永在人间留”。我有幸于2021年10月14日聆听了乐曲在江苏大剧院由张列指挥南京民族乐团的首演,后再于2023年3月30日“上海之春”期间聆听了同样阵容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再度演出,深感通过琵琶的轻抚,苏潇把秦淮河畔湖光山色的四季用极富水墨的文人气质予以舒展。这是一版古风浓浓的四季。
如果说苏潇的灵感来自莫愁湖,那郭鸣的灵感则来自于杭州西湖。任教于浙江音乐学院的作曲家郭鸣自2017年起便为西湖的四季创作钢琴三重奏,至2020年已著有春夏两部,他将于今年完成《西湖·四季》。作于2017年的《西湖·春》有着色彩斑斓的和声、简洁明快的节奏和委婉动听的旋律,描绘出湖水波光粼粼、百花争奇斗艳的画卷。作于2020年的《西湖·夏》以越剧《白蛇传》中的唱段“西湖山水还依旧”为素材。我有幸于2022年11月19日在上音歌剧院举行的上海当代音乐节聆听了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乐团演奏该曲。郭鸣笔下的四季并非仅仅是景色描绘,更多是寄情于景。这是一版内心涌动的四季。

郭鸣《西湖·夏》在上音歌剧院演出
青年作曲家文子洋的《中国四季》结合了情景描绘,具有与维瓦尔第《四季》等同的编制和篇幅。他早先在蓉城之秋音乐节上便有作品由吕思清及其团队演出,过人才思受到吕思清的经纪人刘益生倾慕。2024年,刘益生萌发创意,以中国人写的四季取代皮亚佐拉,与维瓦尔第组成“八季”,遂委约文子洋着笔。作品写成后先后于长沙和武汉等地演出,现又于4月3日登陆上海。
与此前我聆听的文子洋的实验性表达有所不同,《中国四季》可谓是作曲家走出学术象牙塔,充分考虑到听众心理的成熟作品。十二个短小的乐章被均匀地分布在四首协奏曲中,每首三个乐章描绘一个季节。作曲家以农历入手,贯穿节气,四季始于元旦,终于除夕,乐章的划归不再受制于“快-慢-快”的束缚,而是以递进关系关乎气候发展。比如在第二首协奏曲《夏》中,三个乐章分别以仲夏、初夏和大暑为题,循序渐进。第三乐章大暑中,作曲家通过简单音型的快速重复作为酷热难当的直意快陈,无疑是对在维瓦尔第时代尚不突出的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警示。
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品中显而易见的中国元素。文子洋大胆引用京韵大鼓、内蒙古和西藏民间小调,塑造出神州四季的博大精深,颇具鲍元恺或盛宗亮的底蕴。乐曲也有轻松幽默的一面,《秋》的第一乐章是一首圆舞曲,让人念想到肖斯塔科维奇笔下不失鬼魅的华尔兹。诸如泛音和拨奏的使用都让这部作品流露出强烈的现代气息。
《中国四季》可否取代皮亚佐拉与维瓦尔第构成“八季”被大众广泛接受,尚待时间验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子洋用极具东方色彩的笔绘勾勒出中西文化沟通的宝贵桥梁。维瓦尔第所生活的威尼斯不仅是马可波罗的故乡,更是海上丝路在欧洲的起点,它的另一头连接着中国。从威尼斯到文子洋,从维瓦尔第到《中国四季》,年轻作曲家用音乐架起新的彩虹桥,书写着《四季》古今的吟唱和东西的对话。(作者系资深乐评人,澎湃新闻·上海文艺学术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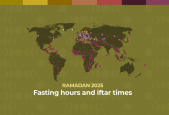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