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丨阐释学的内涵与意义——张江《阐释学五辨》序
- 职场
- 2025-04-19 13:14:06
- 16

《阐释学五辨》,张江著,中华书局,2023年版
自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观念提出以后,告别模仿、自我做主等表述便一再出现。然而,大致而言,除了慷慨陈词之外,学界真正潜下心来从事创造性研究并致力于学术积累的,却并不多见。在这方面,张江先生对阐释学的“阐释”,无疑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建设性工作而独树一帜。尽管在其论著中没有很多字面的“吁请”和“主张”,但其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努力,却展现了值得关注的进路。
在现代哲学中,解释学或诠释学、释义学(Hermeneutics)无疑构成了重要的流派。经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哲学家的系统阐发,解释学已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其影响所及,亦包括中国哲学,在中国学界中,建构“中国诠释学”的主张时有所闻,便表明了这一点。确实,哲学研究既涉及“源”(包括社会文化的背景),也关乎“流”(思想的衍化过程),从“流”的角度看,哲学的反思离不开对以往思想发展成果的回溯,而历史上的思想成果总是以文本为载体,文本的理解则需要解释或诠释。就此而言,解释学或诠释学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对后者也应当予以必要的关注。解释学提出的解释前见,注意到了已有知识结构在进一步的文本理解中的作用;其有关解释循环的观念,肯定了理解与存在之间的循环,这种循环呈现某种本体论的向度:海德格尔曾认为解释学循环体现了“此在自身的生存性前结构”(the existential fore-structure of Da-sein),此种表述也以思辨的方式确认了理解过程与人的存在之间的互动。事实上,理解既是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又可以视为这种方式的具体运用。
然而,将西方的诠释学奉为圭臬,试图依照其形式建立中国的诠释学,则显然有依傍之弊,其主张似乎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西方的诠释学源于圣经解释,其晚近的发展则与现象学相关,这一理论背景决定了它不仅难以避免思辨、抽象的趋向,而且与中国思想衍化的历史形态存在某种隔阂和差异,简单地迎合与复制,既与思想的创造性相悖,也因游离于相关的历史形态而无法获得现实的生命力。从其形成来看,文本或文献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的民族、地域相联系,并呈现相应的空间性或地域性,文本的理解方式,不能无视这一前提。
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上包含创造性内容的文本或文献又具有普遍意义,后者使之同时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思想资源。承认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在面对历史文献的过程中,需要形成开放的视野。眼界的封闭,常常会对文本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定,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敞开其意义,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不断地昭示了这一点。广而言之,在沉潜于以往文本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具体了解以往的思想家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由此提升解读者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在面对以往文本之时,我们总是穿越历史的时空,与作为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的文本作者展开某种形式的对话。以往的思想家通过文本而提出后世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问题同时又激发我们更为深入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解读者一方面可以领略以往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又与历史上的思想家形成思想的互动;文本的理解与观念的激荡在这里相互交融。
以往的文本同时具有价值的意义。包含多重思想资源的历史文本不仅提供了前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知,而且包含着世界和人应该走向何方的价值观念。从逻辑的层面看,“世界是什么”与“世界应该成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无法截然相分。同样,“何为人”与“成就何种人、如何成就人”,也相互关联。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具体体现于他们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通过解读和诠释这些内容,同时可以对其中蕴含的价值意识与规范内容获得某种理解。在接触以往文本并与作者对话时,我们常常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通过深切地领略其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将进一步推进成己与成物的过程。
就观念的发展而言,以往的文本作为思想的沉淀,同时也为思想的进一步演进提供了前提。历史地看,人类思想的衍化,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正是不同的历史文本的前后传承,使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成为可能。这一过程在现在依然没有中断:以中国文化和思想而言,今天同样面临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问题。历史中的文本构成了思想与文化进一步演进的条件: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从无开始,而是需要以已往的发展成果作为出发点。蕴含于经典之中的思想内容,同时也由此成为今天生成中国思想新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很多历史文本虽然已逾千年,但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仍在不断展示其思想的魅力。作为历史智慧的沉淀和结晶,这些文本也为现时代文化发展与思想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以此为前提考察张江先生在阐释学方面的探索,可以进一步理解其意义。与简单地“依傍”西方解释学或诠释学不同,张江先生以“阐释学”这一概念,展示了思想的创造性:在哲学上,新的理论学说往往需要基于新的概念。这一思想系统特别强调了阐释的公共性,突出了文本阐释的普遍性之维。本书可以视为张江先生在“阐释学”方面工作的综合体现,通过对阐释学核心概念的深入辨析,这一著作也使“阐释学”以更系统、清晰的形态呈现出来。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形态的自觉建构,本书首先基于中国传统文本中的文字的考证和疏解,以“阐释学”的关键词之一“阐”而言,作者的疏证不仅基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等传统文本,而且广泛地参照了《汉书》《淮南鸿烈》《十三经注疏》《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献,对过去较少留意的“阐”与“诠”之别做了细致考察,并由此分梳中国古代两条不同的阐释路线,这一论述体现了实证层面的切实性;同时,作者又注重中国传统思想的义理阐释,如从“主体间性”“目的观”出发分析和论述“阐释”思想,由此为阐释公共性的思想提供了内在理据,并呈现了深沉的理论意义。以上二个方面的结合,为“阐释学”奠定了中国的根基。此外,作者并未自限于地域或本土的立场,而是呈现较为宽广的理论视域,并对当代西方的解释学作了理论上的借鉴,在此意义上,该著作也具有某种范围中西而进退之的意义。
我与张江先生素未谋面,但通过他已发表的论文,对其研究工作和进路也有所了解,这一学术关联也许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以文会友”。欣悉张江先生的相关论文将结集出版,特撰以上文字,以为序文。
本文为作者所作《阐释学五辨》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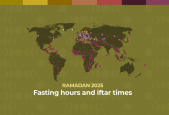







有话要说...